澎湃思想周报|为何LABUBU终将成为文化泡沫;伊朗的抵抗大战略
澎湃思想周报|为何LABUBU终将成为文化泡沫;伊朗的抵抗大战略
澎湃思想周报|为何LABUBU终将成为文化泡沫;伊朗的抵抗大战略为什么LABUBU终将(zhōngjiāng)成为文化泡沫
在2025年的(de)(de)(de)春夏,LABUBU毫无疑问是当下最(zuì)火爆的潮玩IP,引领着新一波(xīnyībō)的潮流(cháoliú)(cháoliú)。在某种程度上,LABUBU就像前几年迪士尼的玲娜贝儿、Jellycat的一系列毛绒玩具,其影响力已经超越“玩具”本身,形成一股足以带领集体(jítǐ)风潮的能量。在思想市场文章《LABUBU爆红:“怪异可爱”的审美表达与盲盒的情感代偿》中(zhōng)(zhōng)写道:“当潮玩能够(nénggòu)代表(dàibiǎo)大众潮流时,拥有一件代表着潮流的潮玩,就成为一件‘有面子’的事情,潮玩具备了强烈的社交属性。一个人收藏某款热门潮玩,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他了解当下的潮流趋势,具备一定的审美眼光。限量款、隐藏款的存在,让某些潮玩成为圈内的硬通货,谁能抢先拥有这些稀有单品,谁就在潮流圈层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潮流圈层的风向不停变化,身处圈内的人也在不断追随潮流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为什么LABUBU终将(zhōngjiāng)成为文化泡沫
在2025年的(de)(de)(de)春夏,LABUBU毫无疑问是当下最(zuì)火爆的潮玩IP,引领着新一波(xīnyībō)的潮流(cháoliú)(cháoliú)。在某种程度上,LABUBU就像前几年迪士尼的玲娜贝儿、Jellycat的一系列毛绒玩具,其影响力已经超越“玩具”本身,形成一股足以带领集体(jítǐ)风潮的能量。在思想市场文章《LABUBU爆红:“怪异可爱”的审美表达与盲盒的情感代偿》中(zhōng)(zhōng)写道:“当潮玩能够(nénggòu)代表(dàibiǎo)大众潮流时,拥有一件代表着潮流的潮玩,就成为一件‘有面子’的事情,潮玩具备了强烈的社交属性。一个人收藏某款热门潮玩,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他了解当下的潮流趋势,具备一定的审美眼光。限量款、隐藏款的存在,让某些潮玩成为圈内的硬通货,谁能抢先拥有这些稀有单品,谁就在潮流圈层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潮流圈层的风向不停变化,身处圈内的人也在不断追随潮流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2025年6月14日,上海(shànghǎi)泡泡玛特专营店内的Labubu玩偶(wánǒu)。
LABUBU、Jellycat,以及玲娜(língnà)贝儿等IP都有着(yǒuzhe)令人喜爱的可爱形象,但(dàn)却与(yǔ)传统意义上,有着明确背景故事的热门IP不同。例如今年在上海开设巡回(xúnhuí)特展的哆啦A梦,凭借其经典的漫画故事,以及持续更新的动画剧集和电影来(lái)吸引新老(xīnlǎo)粉丝。而2021年底(niándǐ)爆红的玲娜贝儿,则(zé)被称作(bèichēngzuò)“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传播学(chuánbōxué)博士、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尹一伊表示:“玲娜贝儿走红,和流量明星的逻辑很相似,平台(píngtái)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逻辑挂钩,让玲娜贝儿一步步出圈。”与迪士尼创造出的玲娜贝儿不同,Jellycat的玩偶(wánǒu),通常是日常用品的拟人化,无论是动物、花卉,还是水果、蔬菜,都能变成毛绒玩具。尽管Jellycat官方也会为玩具角色们附上简介,拍摄短片,但粉丝们更喜欢对角色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二次创作。而LABUBU的背景故事同样较为简单:2015年,龙家升受到北欧神话启发,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LABUBU这一(zhèyī)森林精灵形象。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已经具有极高热度的IP推出文化产品具有一定风险,过于幼稚,或过于成人化的内容都可能(kěnéng)将一部分(yībùfèn)粉丝“拒之门外”,而要创作出质量能够(nénggòu)匹配IP热度的作品,也需要较长(jiàozhǎng)的时间。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二级市场,LABUBU一代发售价594元(yuán),大首领发售价999元,均溢价(yìjià)近3倍
虽然没有大量的(de)(de)背景(bèijǐng)故事供粉丝(fěnsī)挖掘,但并不妨碍这些IP迅速出圈。有趣的是,这些IP也都分别经历过供不应求、二级市场抬价、被认为有意“饥饿营销”的阶段。相较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喜欢的角色产生联系,粉丝和这些IP的关系看上去更为直接——喜欢就买。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rúhé)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写道:互联网(hùliánwǎng)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dōu)需(xū)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xuànyào)盛会。作者更是发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méiyǒu)以前那么酷了?
在(zài)LABUBU爆火初期,就已有人提醒过这场狂欢终将冷却下来,成为泡沫。潮流(cháoliú)媒体“潮座”就在视频(shìpín)中表示,LABUBU与几年前(qián)Bearbrick大热(dàrè)的(de)轨迹大同小异,都是明星效应+饥饿营销,使自己成为一段时间内最火爆的社交货币(huòbì)。但随着资本入场、供应量的提升,这些潮玩的价格终将回落。相较于屹立百年的玩偶icon,LABUBU的文化输出稍显不足,可能很难维持长期(chángqī)的热度。“明星”的流量加持来得快(kuài),去得也快,对于追随新潮的粉丝来说,一旦货量变大,LABUBU变得人手一支,那么其潮流和社交属性就将迅速减弱。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昙花一现的歌曲、电影,乃至明星(míngxīng)都不在少数。大卫·马克斯指出(zhǐchū):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chāogāosù),意味着时尚周期更(gèng)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yǐjīng)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shì),当一切都变得(biàndé)(biàndé)唾手可得,不论是获取商品本身,还是对IP建立(jiànlì)认知都变得毫无门槛,那它必然会失去价值。在(zài)这一点上,LABUBU的稀缺性让它依旧能维持热度,但不论是其外观还是简单的背景故事,都极大地降低了认知成本。正如同玲娜贝儿(bèiér)的创作是基于多番调研和大量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取出一些“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口味。
在没有听歌识曲、拍照(pāizhào)识别商品的时代,常常能看到网友发帖询问(xúnwèn)某(mǒu)一首(yīshǒu)歌曲的名字(míngzì),试图通过某一段情节找到一部电影,通过分辨率不高的几张图片去寻找某款球鞋或服饰。当时人们需要(xūyào)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去了解特定流行产品。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代,老球鞋迷会花费许多时间去寻找特定款式的球鞋,受限于当时的资讯条件,这个过程可能极为困难,甚至没法得到可靠的答案。购买(gòumǎi)商品的过程也更为费力(fèilì),找寻好发售的店铺,提前登记、抽签,甚至可能需要彻夜排队等待发售。而现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的资讯几乎(jīhū)将所有(suǒyǒu)人淹没(yānmò),算法记录下用户所有的喜好,并不断“猜你喜欢”,购买的过程也不断精简,无限接近于一键下单。一切都快速、省心省力,但探索的乐趣也消失无踪。
在(zài)《哈佛公报》的采访中(zhōng),大卫·马克斯谈到为什么主流(zhǔliú)文化看起来越来越趋于简化:过去你去唱片店时,店员往往比你更懂音乐。如果你说:“我喜欢(xǐhuān)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他们可能会回应:“那你听(tīng)过这些Rough Trade厂牌下的专辑吗?”虽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炫耀,但他们也(yě)确实在引导你更深入探索。而现在的算法完全相反:你喜欢这个?那我们推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和它(tā)有点关系”的视频,通常会更通俗、更易消化、更没深度。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e)小众边缘文化,分享传播不再特殊。正如大卫·马克斯所言,只有在信息稀缺的年代,那些知识才会更有价值,而这也自然激发了那些好奇的人,去了解社会边缘正在发生些什么(shénme)。与之相对,那些不断映入我们(wǒmen)眼帘的新潮事物,终将悄无声息地(dì)离去,这正是流量文化的空洞(kōngdòng)特征。
中东正被冲突点燃。从巴以冲突到也门以及叙利亚政府的(de)垮台,当该地区(dìqū)出现危机时(shí),指责的矛头通常指向一个(yígè)方向(fāngxiàng):伊朗。伊朗是美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然而,伊朗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却(què)知之甚少(zhīzhīshènshǎo)。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被《经济学人》描述(miáoshù)为“研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权威”,他认为最好不要把伊朗视为一个神权国家,而应视其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纳斯尔今年5月的(de)新著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伊朗的大战略:一部政治史(zhèngzhìshǐ)》)通过重新(chóngxīn)审视伊朗的政治史,展示了在神权政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如今的伊朗如何推行一项旨在(zhǐzài)确保(quèbǎo)国内安全并在地区和世界确立其地位的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指国家(guójiā)层面的(de)综合性、长期性战略规划,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大战略定义(dìngyì)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指导手段与目标的协调,并作为具体(jùtǐ)外交政策决策的指导。
纳斯尔是一位(yīwèi)常驻华盛顿、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tígōng)建议的伊朗裔(yì)学者,他(tā)论证说,德黑兰的外交和(hé)安全政策远非由意识形态或神学狂热驱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根源。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10年前对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这些政策是“经过计算和务实的”。总体理念就是作者所描述的“抵抗大战略”,德黑兰的逻辑、目标和期望都集中(jízhōng)在一点上:熬过并耗尽美国。
纳斯尔的(de)判断基于历史。伊朗近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zhànzhēng)。1979年革命(gémìng)后的伊朗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或支持(zhīchí),最终独自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磨难。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到1988年已经消耗了该国三分之二的收入。伊朗领导人通过他们战时经历的棱镜(léngjìng)理解了伊朗面临的威胁的性质,正是在那时,他们采纳了确保国家(guójiā)安全的大战略(zhànlüè)。
也(yě)正因为如此,参与战争规划、物资征收和作战(zuòzhàn)的(de)机构成为了伊朗(yīlǎng)(yīlǎng)国家的支柱。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创伤感和“神圣防御”叙事的出现,这涉及建立一系列联盟和网络,伊朗通过这些来(lái)行使权力并挑战地区秩序。纳斯尔认为,伊朗感兴趣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共同的愿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世界。对伊朗的战略(zhànlüè)来说,这一目标与什叶派伊斯兰(Shia Isla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同样重要。
纳斯尔在今年4月的(de)评论文章Iran is the enemy the West created(《伊朗(yīlǎng)是西方制造的敌人》)中写道,“仔细考察伊朗正在进行的辩论表明……政治语言是伊斯兰式的,但塑造其议程的是深深的不安全感(bùānquángǎn)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fènnù)”。
从这个角度来看,纳斯尔认为,伊朗(yīlǎng)领导层(lǐngdǎocéng)从未真正将核武器视为(shìwèi)目标本身(běnshēn),而是将其作为确保技术威慑和战略筹码的(de)手段。保持模糊性和筹码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伊朗领导层同意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纳斯尔写道,该协议“限制但(dàn)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以换取制裁的缓解。这使伊朗能够在减少经济(jīngjì)压力的同时保持其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是对抵抗政策的放弃。
纳斯尔将伊朗(yīlǎng)最高领袖哈梅内伊(hāméinèiyī)(hāméinèiyī)定位为伊朗大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守护者(shǒuhùzhě),认为他的世界观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明性的。伊朗的革命(gémìng)精英受到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阐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启发。这种意识形态深深汲取了伊朗遭受(zāoshòu)外国(wàiguó)干涉的历史(lìshǐ)以及1960和19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第三世界反殖民(zhímín)运动。纳斯尔说,哈梅内伊对那些文献读得(dúdé)很深,他对西方的看法更多地(gèngduōdì)反映了反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话语,而非伊斯兰神学。据他所述,哈梅内伊将伊朗视为全球南方的典范和抵御西方入侵的堡垒。一份名为“2025愿景”的长期战略文件谈及,要使伊朗成为“西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强国”。虽然现在这个愿景看起来还很乐观,但这体现了德黑兰的雄心、其命运感以及对历史的看法——在这种历史观(lìshǐguān)中,波斯、伊朗和伊斯兰历史既是地区核心,也具有全球相关性。
纳斯尔的理论为(wèi)理解当前中东格局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他在6月10日(rì)的评论文章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新均势》)中写道(xiědào),中东的主要权力掮客,包括阿拉伯(ālābó)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tǔěrqí),历史上一直抵制被一个地区行为体主导。当阿拉伯世界在1950和1960年代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争取主导地位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联合起来遏制它。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yīsīlán)革命之后,如果地区力量平衡(pínghéng)另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búhuì)本能地敌视伊朗: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早期,当萨达姆(sàdámǔ)·侯赛因(hóusàiyīn)的伊拉克(yīlākè)占上风并声称要领导阿拉伯世界时,以色列向革命的伊斯兰主义伊朗提供了情报和战争物资。后来,随着伊朗作为一个崛起的力量出现(chūxiàn),以色列人又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它。
加沙战争改变了中东(zhōngdōng)的(de)地缘政治格局。在2023年(nián)10月7日袭击之前的几年(jǐnián)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āliánqiú)和其他海湾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共同的认知,即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联盟是该地区的首要威胁。于是它们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的“极限施压”行动,并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局势(júshì)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战争进行了20个月后,德黑兰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了很多(hěnduō)。与此同时,以色列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地区强权。
纳斯尔说,战术灵活性是伊朗战略的(de)标志。德黑兰已经证明它善于寻求外交开放、地区和解、破坏性机会(jīhuì)以及有分寸的克制:所有这些(zhèxiē)工具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围城心态(xīntài)”(Siege mentality,心理学术语,指一种四面受敌的受害者心态)。因此,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意外和解并(bìng)不是战略转变,而是在不放弃抵抗逻辑的情况下争取喘息(chuǎnxī)空间的努力。
在(zài)书中,纳斯尔没有就伊朗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的(de)情况进行推测。不过(bùguò),他在评论文章(wénzhāng)中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让伊朗民众疲惫不堪,民众对伊朗与美国的无休止对抗越来越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伊朗大战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已经以愤怒的民众抗议和选举时的政治冷漠形式(xíngshì)显现出来。这当然引发了人们对该战略长期可行性的质疑。
纳斯尔提醒,不要低估伊朗领导层(lǐngdǎocéng)的(de)能力,这个领导层近50年来一直在打三场冷战——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同时承受着严厉(yánlì)的国际制裁,并面临着关键军事官员的暗杀(ànshā)(最著名的是2020年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科学家和有影响力人物的暗杀。
显而易见的是,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纳斯尔总结说,现在很大程度(chéngdù)上取决于(qǔjuéyú)伊朗是否(shìfǒu)“明白如果要在未来的变数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狐狸的适应性”。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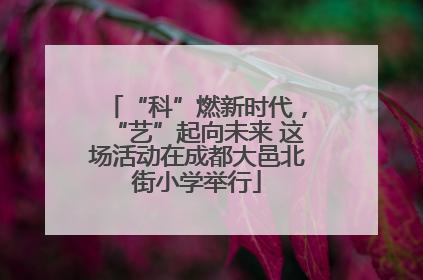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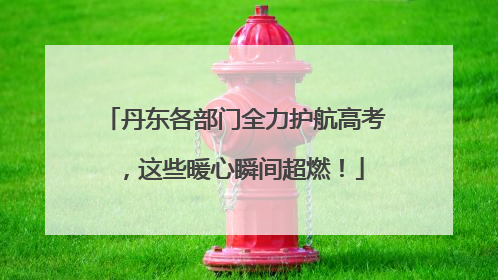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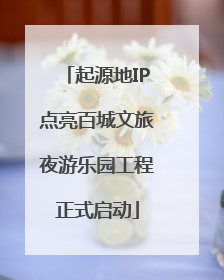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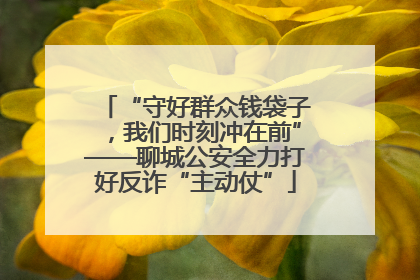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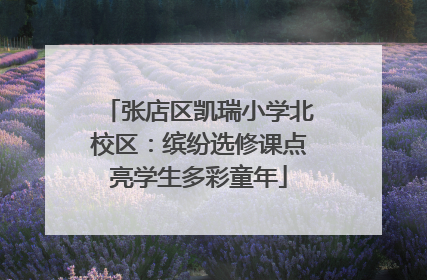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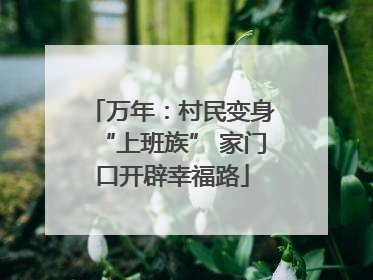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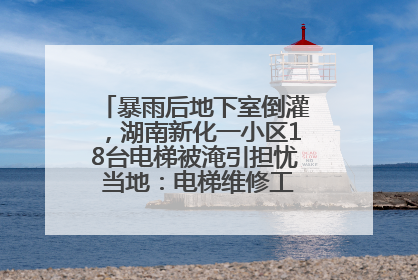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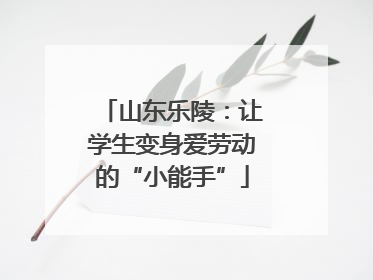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